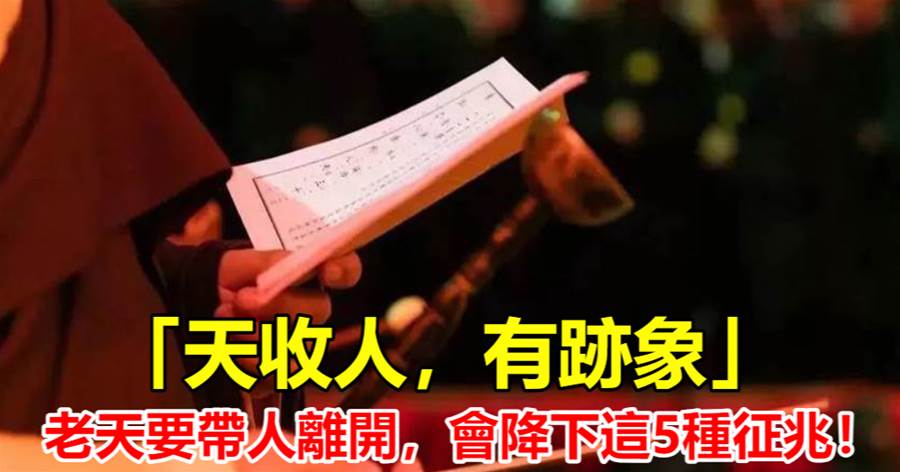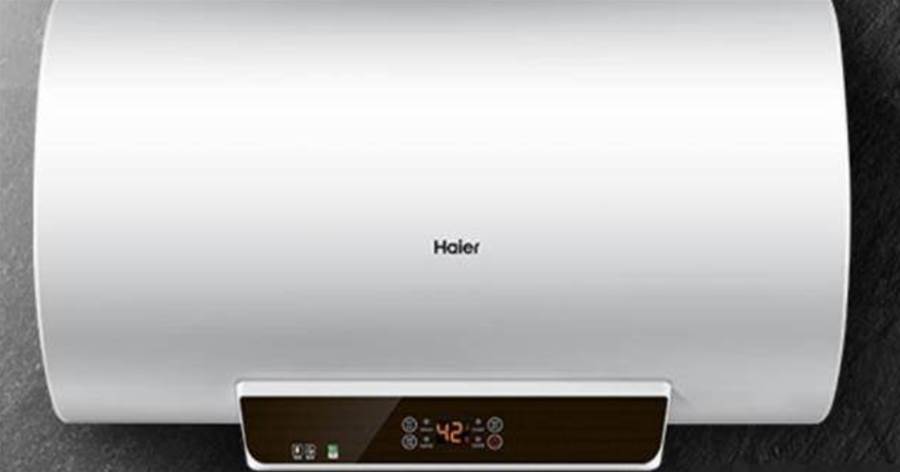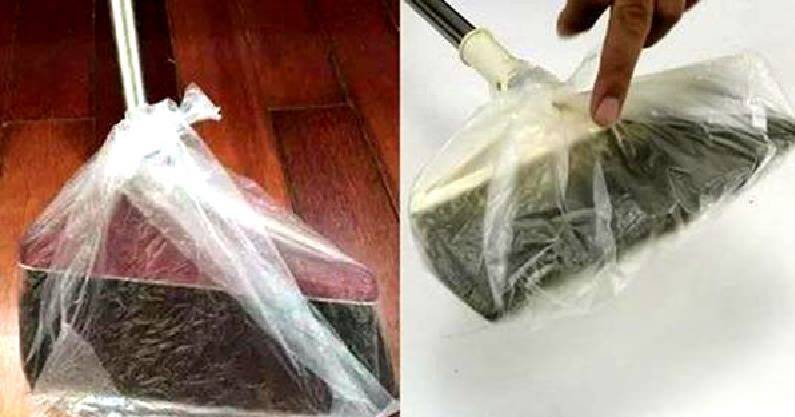上週在皮膚科門診遇到的那對父母,讓我想起從醫這十年來,見過的各種「教養表演」——尤其是那些把「西方理念」掛在嘴邊,最後卻讓孩子遭罪的家長,總讓人忍不住搖頭。

那天上午,第一位病人是個國小一年級的男孩,手上長了好幾顆病毒疣,需要做冷凍治療。陪他來的爸爸一進診間,就先遞給我一張列滿「注意事項」的紙條,開口就是:「醫生,我跟孩子溝通好了,他知道要治療,但我們不強迫,要傾聽他的感受,不能讓他有心理創傷。」
我點點頭,看著爸爸蹲在孩子面前,用極其溫柔的語氣說:「寶貝,等下醫生叔叔用棉花碰一下,有點涼涼的,就像吃冰一樣,不怕喔?你要是緊張,就告訴爸爸,我們可以停下來。」孩子似懂非懂地點頭,小手卻緊緊攥著衣角。

結果我剛拿起沾了液態氮的棉籤,孩子突然「哇」地一聲哭出來,掙扎著要把手縮回去。爸爸立刻衝過來按住我的手:「醫生等一下!他還沒準備好,我們要再溝通!」接下來的半小時,這樣的場景反覆上演三次——爸爸跟孩子談心、約定、保證,孩子表面同意,一見到棉籤就瘋狂尖叫。
我後來請他們去走廊再調整,爸爸還特意跟我強調:「歐美國家都這樣,不能強制孩子,要讓他自主選擇,不然會留下陰影。」最後眼看快到午休時間,爸爸只好帶著孩子離開,治療沒做成,臨走前還說:「明天我們再來,慢慢溝通,總能讓他接受。」

隔天上午,孩子的媽媽帶他來了。跟爸爸的謹慎不同,媽媽一進診間就把孩子抱到治療椅上,讓他面朝自己,然後用雙臂把孩子的手腕牢牢固定在腋下——孩子哭得臉紅脖子粗,腳亂踢,卻連手指都動不了半分。媽媽對著我說:「醫生,麻煩快點,他哭一陣就好,別耽誤時間。」
我抓緊時間用液態氮點在病毒疣上,前後不過十秒鐘,治療就結束了。媽媽鬆開手,從包包裡掏出一顆草莓糖遞給孩子:「你看,是不是很快?哭完了就吃糖,等下媽媽帶你去買漫畫。
」孩子抽噎著接過糖,沒幾分鐘就靠在媽媽身上,開始聊想要哪本漫畫,剛才的哭鬧像沒發生過一樣。

後來孩子復診時,我問起這事,媽媽才笑著說:「他爸爸就是太執著那些『教養理論』,以為跟孩子磨時間就能解決問題,結果前天晚上孩子因為怕治療,連飯都沒吃好。其實孩子年紀小,哪懂什麼『自主選擇』,他只知道會痛、會害怕,這時候需要的不是漫長的溝通,是讓他知道『這件事必須做,而且很快就結束』。」
這讓我想起之前遇到的另一個案例:一個五歲的女孩長了霰粒腫,需要手術引流。爸爸堅持「要讓孩子自己決定是否手術」,每天帶孩子來診間「熟悉環境」,跟她解釋「手術是怎麼回事」,結果拖延了兩週,霰粒腫化膿,孩子痛得整夜哭,最後還是媽媽堅持當天手術,才解決問題。術後爸爸還抱怨:「這麼強制,孩子肯定會怕醫生。」可事實是,孩子後來復診,看到我還主動打招呼,說「醫生叔叔,我的眼睛不痛了」。

其實在診間裡,經常遇到這類「理念派」家長:他們會背誦各種西方教育理論,說「不能懲罰」「不能強制」,把孩子的「感受」放在第一位,卻忽略了「健康」才是底線。就像那個長病毒疣的男孩,如果一直拖延治療,病毒疣可能會傳到其他手指,甚至影響握筆;那個霰粒腫的女孩,拖延只會讓痛苦加劇。
這些家長總怕「強制」會給孩子留下創傷,卻沒想過,反覆的恐懼、無謂的等待,才是更大的傷害。就像那位媽媽說的:「孩子需要的不是『無條件順從感受』,是『有人告訴他,別怕,這件事必須做,我會陪你度過』。」

後來我再遇到這類「理念派」家長,還是會讓他們先嘗試自己的方法——畢竟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教養方式。但大多數時候,最後都是家長沒了耐心,或者孩子因為拖延加重了癥狀,才不得不採取更直接的方式。
其實教養從來不是「照搬理論」,而是「因地制宜」。對孩子來說,比起滿嘴的「尊重與自由」,更重要的是有人能在他們害怕時,給予堅定的支持,告訴他們「這件事雖然難,但我們可以一起解決」。
就像那位媽媽,沒有空泛的教養話術,卻用果斷的行動,既解決了孩子的健康問題,也讓孩子知道:有些困難,咬咬牙就能過去。這大概就是最實用的教養吧——不談理念,只做對孩子好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