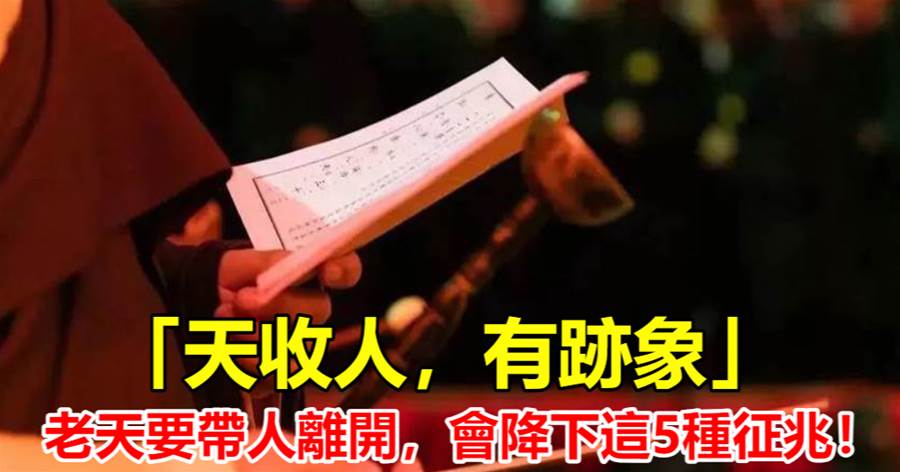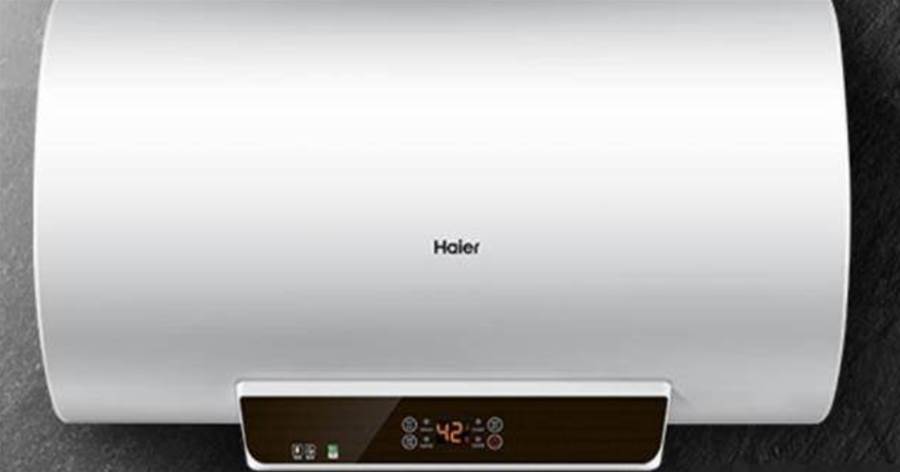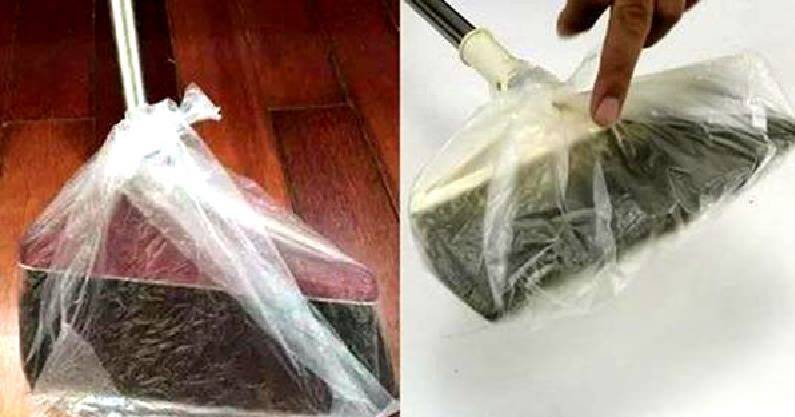「要想不失望,不要抱有期待就好了。」
這是多少人在面對親密關系時的心里話?
就像黛安娜·阿克曼在《愛的自然史》里說的那樣:
「我們把剛剛磨利的刀子交給某人,徹底裸露自我,接著邀請他靠近自己,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怕的?」
不去期待,不去暴露自己,或許就會安全一點。
可是,親密關系又是那麼美好,它意味著我們「可能」被另一個人全然地接納,給予我們想要的放縱、寵溺、和陪伴。
我們一邊害怕期待,卻又難以控制期待之心的升起,這其中的平衡,該如何把握呢?
在最近熱播的古裝劇《長相思》中,楊紫扮演的女主角小夭,也遇到了同樣的難題。

不敢有依戀之心,
我們在害怕什麼?
在《長相思》中,小夭本是皓翎國王姬,跟隨失婚后的母親,來到了西炎國。
母親出征戰死,西炎國王又將小夭送去了玉山修煉。
小夭一直期待著自己的父親皓翎國王和表哥玱玹能夠來接自己回家。
然而她苦苦等待了70年,所有人似乎都早已經將她忘記了。
她獨自跑下玉山,歷經百年顛沛之苦,不但失去了身份,也失去了容貌。
她被囚禁過,被母親的敵人虐待過;她被歧視過,被來往的過客欺負過。
最終,她依靠著自己的力量,逃離了危險,來到清水鎮落腳。
自此以后,她化身小醫師「玟小六」,懸壺為生,恣意不羈,秉持著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」的生存原則,告訴自己絕不能輕易向他人敞開心扉。

直到,她遇見了葉十七。
初見十七,他是個渾身是傷的小乞丐,小夭看見他就像看見當初被虐待的自己,用自己的血救活了他。
朝夕相處的時光里,小夭發現十七是個善良溫柔的人。
他會在她趴在桌上睡覺時,用手背為她擋掉融化的熱蠟;
會記住她喜歡吃的花,每次回家都為她帶上一些;
會提前在她的被子里放上暖爐,為她打掃房間,幫她洗碗……
這些無微不至的照顧,讓小夭動了心。

一次,小夭和外來的神族起了沖突。
原本約定好和她一起對抗的葉十七,卻在她轉身求助的一瞬間,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沒有聽解釋,也沒有原諒,小夭選擇了再次封閉自己。
她自嘲道:
「為什麼我會有依賴別人的想法?
把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,明明知道有多大希冀,就會有多大傷害。
與其這樣,還不如靠自己。就算摔倒,能接住的,只有我自己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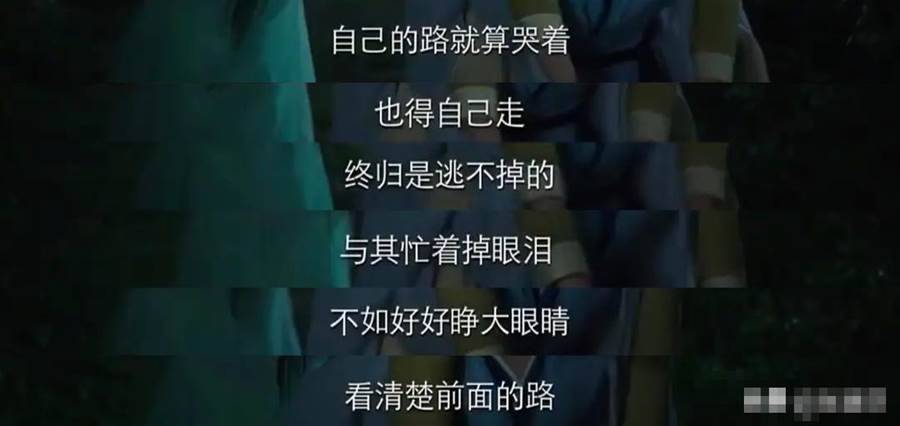
她是如此清醒而又令人痛心,像極了每一個不敢輕易敞開心扉的人。
母親的離開、父親,哥哥的舍棄、到如今,喜歡之人的背叛,令小夭徹底放棄了依戀他人的想法。
每一個經歷過分離的人,或許都有過這種感受,從一開始的不甘心到最后的放棄。
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,這與我們和養育者的依戀模式有關系。
英國心理學家鮑爾比提出了依戀理論,他發現孩子在被迫和母親分離時,會經歷三個階段的反應:
抗議、絕望和疏離。

媽媽剛離開時,孩子會不理解、發脾氣、時刻關注著媽媽回來的跡象;
緊接著,孩子發現媽媽很長時間都沒有出現,懷疑媽媽不會再回來了,而變得退縮和哀傷。
到最后即便媽媽回來了,他們也會表現得漠不關心,仿佛媽媽已經不再重要。
他們開始對外在的東西表現出極大的興趣,玩具、零食等,也就是說,他們不再依賴人,而是開始把這份情感轉移到了物體上。
小夭也是這樣,她依賴著自己的醫術、生意、錢,而不再去關注情愛,希望讓自己從源頭上切斷一切會帶來痛苦的可能。
她逃避著與他人親密的一切可能。
然而這種逃避的背后,其實隱藏的是我們內在沒有被接納的某種渴望。
當渴望不被接納
會衍生3種模式
我們拒絕痛苦、逃避愛情,在表面上割舍了對他人的「依戀」,但內在的聲音無法騙人:
一次次的拒絕,是因為我們害怕傷害的發生;看似是在保護,其實也是在表達深深的渴望。
我們渴望有一個人,能夠治愈這些傷害,將我們從黑暗的泥沼中拉出來。
因此,我們開始尋找一種拒絕與渴望的平衡,在內心衍生出三種情感的模式:
第一種:游戲之愛。
我有一個朋友,將愛情視作一種游戲,她說:
「愛的時候就在一起,不愛了就分開,彼此都灑脫一點,也挺好。」
她覺得愛情就是轉瞬即逝的,不可能天長地久。
所以我們總是看到她很快又換了一個男朋友,但沒有一個跟她走到最后。
她的愛停留在表面,一邊膚淺地享受著所謂的「當下」,一邊拒絕對方真正走進自己的內心。
然而,沒有走進就沒有治愈,她只能在虛假的關系中反復橫跳,無法進入一段彼此成長的親密關系。

第二種:疏離之愛。
顧名思義,這是一種冷漠而疏離的愛。
我有一位來訪者,面對感情總是一副無所謂的態度,在婚姻里,他很少表露自己的情感,也不過多關注妻子,一直很平淡。
到最后,妻子無法容忍這樣的生活,便提出了失婚。
那時的他,也沒有挽留,便答應了。
可有一天,他坐在回家的公交車上,看著窗外來來往往的人群,突然就流淚了。
他想起妻子、想起曾經燈火通明的家,突然覺得心里缺失了很大的一塊。
因為從小經歷了父母的拋棄,他對感情不抱期待,因此,他刻意斬斷了過多的情感連結,讓自己看起來毫不在意,以此來屏蔽害怕產生的焦慮。
然而,情感的滲透是隱秘而悄無聲息的。
在與妻子相處的日日夜夜里,他早就愛上了妻子,甚至偷偷地期待著,妻子能夠走進他的內心,將他從冷漠中抽離出來。
然而,他的沉默和封閉最終還是傷害了這段關系。

第三種:「被需要」的愛。
在這種模式的驅使下,我們明明很想要和他人建立聯系,但是又害怕自己太過依賴別人,于是索性成為「被需要」的那一個。
就像《長相思》中的小夭,她成為玟小六之后,也在嘗試和他人建立聯系。
但她的內心想法卻是:
「如果我是有價值的,被需要的,是不是就不會被拋棄了?」
于是,她開了一家醫館,救死扶傷,還和一個西炎逃兵一起收養了兩個孤兒。
幾個人的生活拮據,但玟小六為了讓收養的孩子能夠娶到老婆,還是會冒著生命危險去采靈藥,換來彩禮;
大家都勸玟小六不要傾心救助不明身份的葉十七,但她還是傾囊教授草藥知識,讓十七有所依靠;
甚至,在相柳需要用她的血救治身體時,她也沒有拒絕。
于是,所有的一切都進入了一個循環。
我們用不同的防御模式,推走了依戀的可能性;但這些模式,實際上又在表達著對依戀的渴望。
我們變得擰巴、糾結,痛苦,焦慮。

其實,要擺脫這種痛苦,關鍵在于我們要看清,自己真正害怕失去的究竟是「依戀」還是我們「期待的依戀」。
比如,小時候我們希望媽媽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不要離開我們,但媽媽總會去上班,總會有自己的事做,但那是不是就代表著,她不愛我們了呢?
當然不是。
只是她沒有用我們所期待的方式來愛我們罷了。
延伸至親密關系之上也是如此。
最好的平衡模式,不是完全否認愛情,而是否認愛情的「完美」。
不必害怕期待,
但要放下「完美」
克里斯多福在《親密關系》中寫道:
「通往地獄之路,是用期望鋪成的,因為期望會把充滿愛意的感覺擋在門外。」
但這并不代表我們要刨除掉對一段關系所有的期待,而是要看清,你的期待背后是否有著對理想伴侶的幻想,以及不切實際的依戀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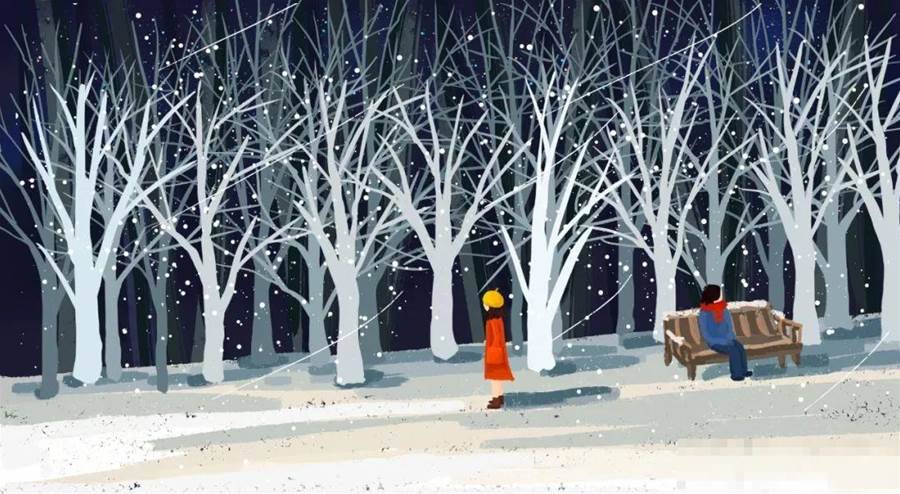
在每一段親密關系里,當你首先在心理上設定高墻,就很難翻越到真實的[兩.性]關系里。
我們會對感情抱有一種「完美」的幻想,稍有不如意,我們就會覺得:
糟糕,被騙了,這不是我想象的關系。
可真實的關系本就是有瑕疵的,我們越是防范這些瑕疵,就越會看到這些瑕疵。
就像小夭對十七,她害怕十七會拋棄自己,會背叛自己,越會去尋找這些蛛絲馬跡來證明「人是不值得依靠的」。
就像,當十七害怕自己真實身份被認出而躲起來時,小夭根本不想聽解釋,而是沉浸在自己編排的背叛戲碼之中。
可是,十七的「背叛」來自于對小夭的愛。
他擔心自己的真實身份被戳穿,就不能陪伴在小夭的身邊了。
或許他的處理方式是有瑕疵的,但他後來全心全意為小夭籌謀,在小夭差點被殺死時傷心欲絕自斷生路,都證明了他的真心。
一個人究竟值不值得我們付出,值不值得我們敞開心扉,只有在真實的關系里才能得出答案。

因為怕而不敢向前一步,困在自己給自己的高墻里,我們就會失去很多美好的體驗。
在踏入關系之前,我們真正需要平衡的,不是不讓自己產生「期待之心」,而是不要讓自己產生「期待完美之心」。
不要在真正的愛情還沒開始時就預設對方應該是什麼樣子,也不要給愛人強加某種設定:
不允許他軟弱、不允許他有自己的思想、不允許他不為你犧牲。
真正的愛情本當承受對方的偶然性,去承受對方的缺點、局限、原始的無緣由。
而要放下對完美的期待,需要從自我出發。
對任何人的期望,實則源自自身的需求,我們應該將重心放在自我滿足身上,而非強求別人體貼自己的心意。

首先,從你對他人的期待里,看見潛意識里的需求清單。
很多時候,我們會對另一半產生很多的期待,其實是在向他輸入你的需求。
當你因為對方不記得你的生日而生氣時,你生氣的或許是他不夠重視你,我們或許并不是真的要對方記住你的生日,而是想以此來證明自己的價值。
那麼,當我們開始有所期待的時候,不妨去問問自己,你到底期待的是被滿足什麼需求?
當你看見這個需求后,就可以再次對自己說:
「這個需求并不是伴侶的職責,而是這個行為,勾起了深埋在我內心的創傷。」
你會發現,你并不是對眼前的這個人失望了,也并不是他沒有滿足你的期待,而是你內心本就存在的創傷開始隱隱作痛了。
看見了以后,你就可以把重心逐漸轉移到自我身上,開始掌控你的內心。

其次,試著對愛人的付出表達感恩。
我們糾結于「完美」,就會糾結于「不完美」,當我們用雞蛋里挑骨頭的心態去尋找愛人身上的不完美時,我們就很難實現接納。
不如將這種心態反轉,不去尋找那些讓我們失望的特征,轉而去尋找那些令我們愉快的特征。
每當發現一個愛人的閃光點,我們就對對方表達感恩。
你可以說:
「謝謝你在忙碌的工作里還惦記著我沒有吃飯。」
「謝謝你聽進去了我的抱怨,并且做出了改變。」
感恩的頻率是強大的,會在彼此的關系里發出共振,你不會再去糾結對方沒有滿足你什麼,而是變得更加充盈。
你會發現,自己本就擁有一切,又何須向他人索求。
當正向的頻率不斷發出,你的愛人也會因此而變得更加溫柔,你想要的偏愛或者是倚靠,也會與你不期而遇。
如此一來,我們才能體會到親密關系里生發的真實的喜悅,祝福大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