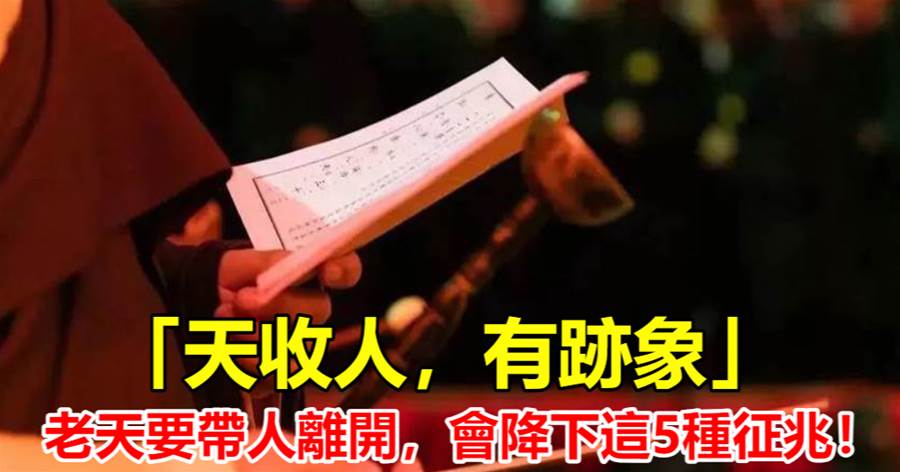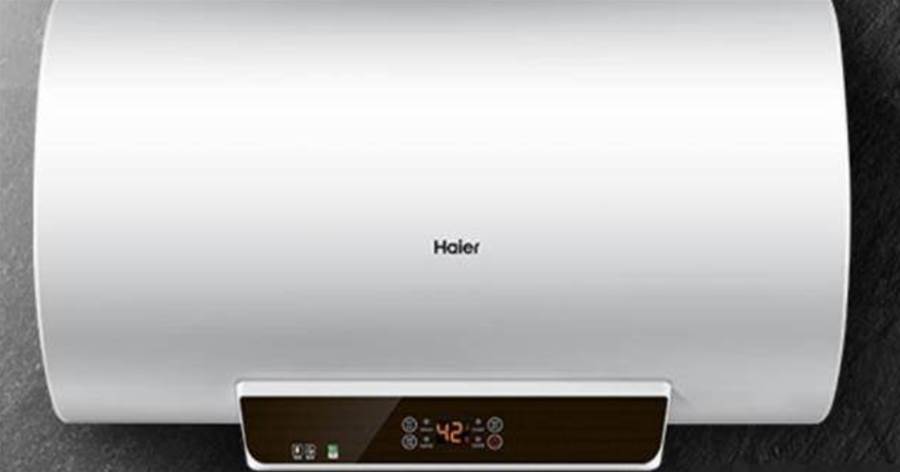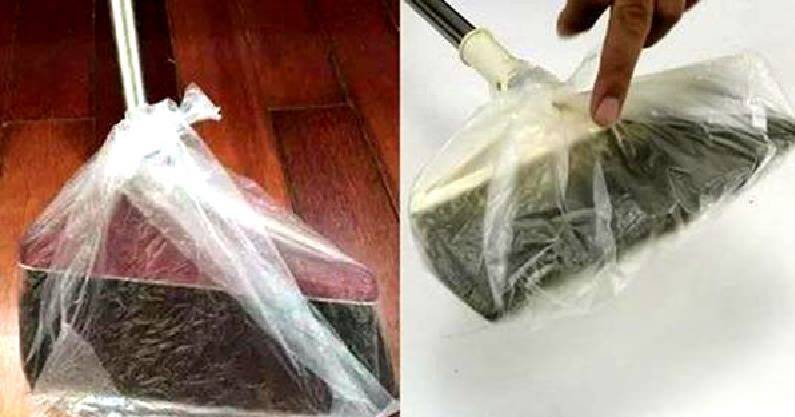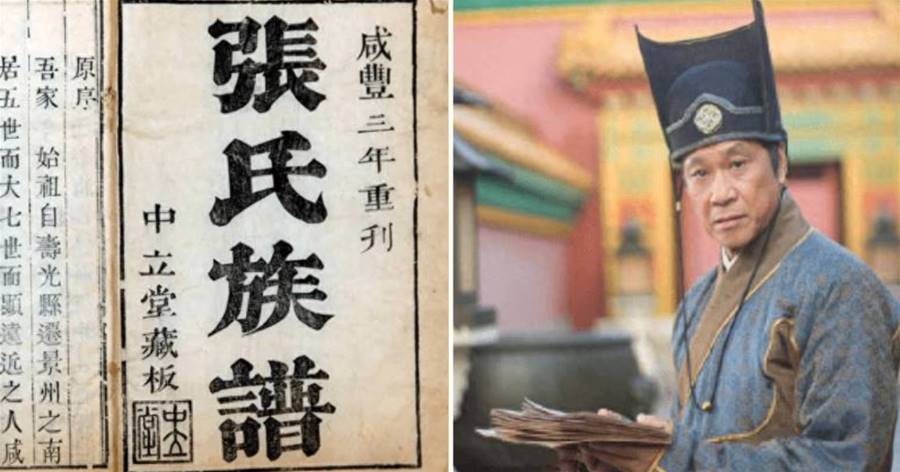
家譜,又稱族譜、宗譜,是中國自古以來一種特殊的文獻形式。
對于一個家族來說,家譜不僅能夠清晰地體現本家的世系繁衍,還用以記錄這個家族的興衰起落——何時繁茂,何時凋敝,從何人開始建功立業、官拜相公,從何人開始不善經營,走向敗落……
古代的家譜和祠堂、宗族聚居地密切相關,更是和祖輩生長的土壤關系密切。

因而,隨著朝代更迭,或者一些戰亂、天災的年代,歷史上的很多家譜就此消滅斷線,許多家族因此無跡可尋。
當今可見的大部分家譜,大多是從明清兩代開始撰寫的。
明清時期,由于統計人口、稅收等需要,加之人口數量和相對位置趨于穩定,統治者非常重視戶口、籍貫等人文資料信息,大多數家族都開始拾起失落的族譜,進行修補,乃至出現了專門替人修撰族譜的「譜匠」職業。

人生須臾百年,唯有史料留存于世。
由清朝所著、記錄明代大致歷史的《明史》也是其中一員。既是史料,自然以極高的真實性成為后人所參考的范本。
然而,后世在福建發現了一部來自明朝一位宦官的家譜,其中的記載竟和《明史》有所出入。

經過進一步的考證比對,其中有出入的事情并不少,甚至一些記載有明顯的趨向不同,這使得后人不禁頓生疑竇:一個是家族自己的家譜,一個是朝代修撰的史書,而對于這些事件的記載,究竟孰真孰假?難道清朝在修編史書的時候,有所隱瞞或者是有所篡改嗎?
且從這位宦官的家族,以及其中記載的一些事件開始講起。
2011年期間,有人在我國福建地區發現了一部家譜,經過勘查了解,確認這部族譜屬于明代的一位有權勢的宦官,其人名叫張敏,這部族譜也因而被稱為《張氏族譜》。

根據族譜記載,張敏其人生于1434年,自幼父母早亡,無人庇佑,尚未成人便遭人算計,害進深宮,成為了一名宦官,但其人在宮中久而得勢,最終在圣眷優厚下,從一個孤苦伶仃的孤兒,成為了皇帝身邊、龍椅之下炙手可熱的人物。
而根據記載,他一生中做過一件最為膽大包天、甚至有可能招致殺身之禍的事:他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,將一位出身撲朔迷離、本該不存在于皇家宗族內的皇子養大成人。甚至這位皇子在之后榮登大統——他就是之后的明孝宗,其名朱佑樘。

明成化時期,明憲宗正執政,作為帝王,卻不慕后宮三千粉黛,而獨獨鐘情于一位萬貴妃,這位萬貴妃本是宮女出身,照顧當時尚年幼的憲宗,而憲宗在這個過程中日久生情,對這位年長于自己的體貼美人傾其所有。
金銀珠寶、榮寵體面,乃至帝王家少見的「一心人,萬貴妃都得到了,可以說是成為了普天下最尊貴的女人。
只是,人生斷不可能毫無遺憾、一帆風順,身負盛寵的萬貴妃,卻始終膝下無子。

帝王家的寵妃,即便再怎麼體面,沒有子嗣傍身都是大忌,畢竟在那個母憑子貴的環境下,一個在后宮無依無靠的女人,終究會走向年老珠黃,而有力奪嫡的一個孩子往往能顛覆整個深宮的局勢乃至前朝的局勢。
萬貴妃自身無子,又怎可能容忍別人靠孩子爬到自己頭上,在她有意的限制和暗害下,后宮的嬪妃竟無一位長成的皇子。
隨著時間的推移,明憲宗本人須發漸白,也不禁感嘆起了自己的命運,認為自己此生恐子孫福薄。

就在這時,他的心腹太監張敏對他叩首跪拜,稱陛下不必過于擔憂,其實這宮內,有一位皇子長成。明憲宗聞言,又驚又喜。
這個孩子便是朱佑樘,一個宮女的孩子,本來萬貴妃在知道宮女有孕后,著張敏將其處理掉,以絕后患,可張敏更在意這個孩子對于無子的皇帝的重要性,便沒有聽從她的話,而是保護這個孩子降生,并且隱瞞這件事直到他長成。
這件事情在悄無聲息中促成,待到萬貴妃發覺時,木已成舟,再沒有轉圜的余地,只得咬碎銀牙咽下這一口氣,卻在心下記了張敏一筆。

這之后張敏憑借這件事,在皇帝面前賺足了好感,深受器重,卻也因為這件事情,被萬貴妃降罪,最終吞金而自逝。
而從這一部分開始,《明史》和《張氏族譜》的記載就出現了出入。
那麼具體有哪些地方記載不一致呢?

首先便是明憲宗的得知朱佑樘身份的時間點,《明史》中記載這件事情發生在1472年,而《張氏族譜》中,這件事情發生在1475年,時間有一定相差,然而看似僅僅相差三年,個中區別卻很大。
因為就在1472年,明憲宗的第一個孩子、先太子朱佑極,年僅三歲而夭亡。
若根據《明史》所言,這個孩子剛剛過世,就扶了第二任太子上位,對于子嗣稀少、對每個孩子都很重視的明憲宗來說,恐怕不太合理。

即便對于朱佑樘的出現再驚喜、再寵愛這個孩子,他也不可能如此快就遺忘先太子,多少應當有所避諱,況且幼子早逝,皇帝悲痛萬分,張敏亦不可能在這個敏感的節骨眼上暴露這個消息,在這件事中,《明史》之記載有不合理之處。
反觀《張氏族譜》所記,三年之后再行冊封,于情于理都顯得更順理成章。
而關于張敏入宮的經歷,兩方又有差誤之處,《族譜》記載其是為奸人所害,不得已而為之,又在真相大白后受到皇帝嘉獎,得以侍奉左右。

而《明史》對此的記載更為平淡,沒有那些跌宕起伏的經歷,而只是因為家貧,幼子無法充公,被迫入宮成為宦官。
根據其他史書的記載比較,《明史》寫的較為中肯真實,《家譜》似乎對此進行了一番修飾和美化——不難理解,家譜畢竟是關乎一個家族的臉面,對于一些不太好的經歷和事件,要極盡寫的模糊一些,修飾得體面一些。
而在年甲疏漏的背后,還有關于繼太子的撫養權問題。

朱佑樘作為皇帝的獨子,又有萬貴妃虎視眈眈,他的收養人自然應該能擔負起保護他的責任。
這一點在《孝宗本紀》中有所體現,其中記載朱佑樘為周太后、也就是皇帝生母所收養,自然萬全。
可是本紀中,對于收養時間的記載就極為模糊,按照當時的律法,只有朱佑樘進入皇家玉牒后才有資格被周太后收養——《孝穆紀太后傳》中,這個時間點就非常明確,是成化十一年,其皇子身份已被承認且昭告天下。

這里的時間點記錄不明,也很有可能是受了先前年甲紊亂的影響。
此外,在《張氏族譜》的版本中又出現了一個以上兩卷均未出現的人物,也就是廢后吳氏。
這位身居冷宮的廢后是明憲宗的發妻,《族譜》中記載她「保抱惟謹」,指出在朱佑樘被發現前,一直是廢后吳氏在照顧他。

最后,有關這位宦官張敏的真實死因,也有不同的記載。《明史》所記載的時間是1475年,而《張氏族譜》所記是1485年。
前者主張張敏系萬貴妃所迫害,吞金自逝;而后者所記是與同僚產生矛盾,一氣之下身患重疾,最終不治身亡。
根據《同安縣志》記載,張敏真正的去世時間應當是1485年,確實是病亡的,縣志里也存留了張敏患病后求醫問藥的一些經歷和資料。

且根據其他史料,朱佑樘回歸正統后,張敏因此獲得殊榮,在皇帝的授意下,盡管萬貴妃可能會找他的麻煩,也大不至于不顧皇帝顏面將其逼死。
至此,這幾件事的記載不同,已經足以得見兩部資料之間產生了一定的差別。
而這種出入之處,是否會影響到這兩份資料的嚴謹性和可靠性?造成這種出入的原因又有哪些呢?

后世根據其他人物傳記、當地縣志等資料對當年的時間進行了梳理和還原,在這個過程中,發現《明史》的記載有一些自身相悖之處,從邏輯上略有不通順,因而在這一點上,有的后世學者懷疑其中存在清朝刻意模糊、篡改前朝歷史的可能。
然而,這個觀點很快不攻自破,因為《明史》的記載十分繁雜瑣碎,如果清朝統治者有意通過這種方式來干涉歷史記錄,更應該力求邏輯自洽、起碼不應該出現與自身相悖的蹩腳失誤,讓后人輕易就看出不對勁。

結合清朝史書修撰的條例和方式,更可能的情況是:由于《明史》修撰時間長且時間跨度極大,耗費了很長時間,且史料出處不同、執筆亦非同一人所為,執筆者在修撰期間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換過數次,才將這部史書寫完。
許多歷史事件和關鍵時間點,都隨著資料的遺失和當事人的離去而變得撲朔迷離,一些細節后人各執一詞,史官亦難決斷。

當不同的史官接觸了不同的史料、并且對歷史的還原不能達到一致時,就可能會出現這種前后不一、邏輯不通的情況,畢竟每個史官的記載撰寫思路都必然有所差異。
況且史書畢竟是有選擇的記載歷史大事,根據撰寫目的、撰寫對象的不同,也會有不同的潤色和偏向:
記錄前朝的歷史,當朝者必然不能使其十全十美,凌駕于本朝之上,但由于是專門的史官撰寫,規模和詳細程度都很高。

記錄家族興衰的族譜,寫盡家族的榮寵衰敗,不可能做出自敗門楣的事,所以傾向于對自家人有所美化,但也更容易記下當事人涉及的事件真相和秘密。
寫當地的縣志,對于該地各家族的姓氏、往來、功名都有詳盡的記載,但迫于地方官員的勢力,偶爾會忽略一些當地管理生活中出現的問題。
寫各人的傳記,自然可以找到一些人物光鮮以外的另一面,使被記載者更加完整,卻傾向于忽略他人對一些事件的影響和建樹……

由此可見,歷史悠久,后人無法真正親身經歷那些朝代的故事,故而要在浩如煙海的史書中比對、篩選、拼湊推理,這自古以來就是一份艱巨而繁重的工作。
《張氏族譜》所記雖然有顛覆性,卻并不會影響《明史》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因為古人有云:「以史為鑒,可以知興替。」

除了真實性,史料還具有的一項重要特征,就是幫助后人總結前人經驗,盡量揚長避短,一些記載上的疏漏并不會就此影響《明史》的教育性和對于后人的啟發,故而《明史》之失誤,既不能說是清朝故意而為之,也不能武斷地說其就此喪失了史料價值。